学术成果 | 《敦煌通史•两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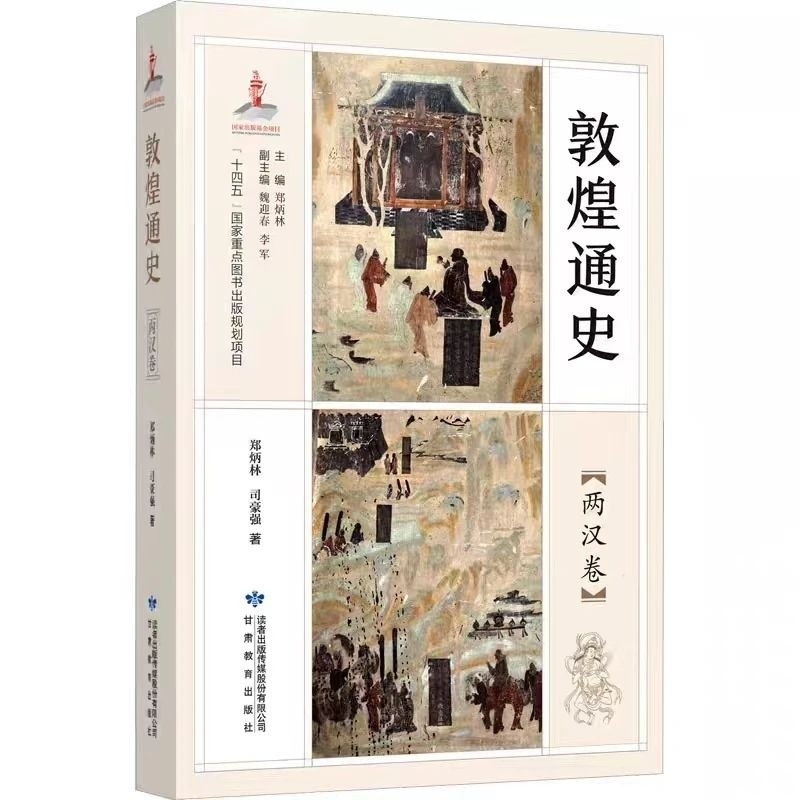
书名:敦煌通史•两汉卷
作者:郑炳林 司豪强
出版社: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内容简介
本书作为《敦煌通史》的两汉部分,以专题的形式对汉代敦煌历史做了贯通性的梳理。“两汉敦煌郡的主要定位之一就是作为汉朝中央政府经营西北地区的军事基地”,本书以此为核心视角展开论述;悬泉汉简、马圈湾汉简和居延汉简等西北汉简是研究两汉敦煌历史必不可缺的参考文献,本书采而依之;此前学界关于汉代敦煌的研究偏于碎片化,本书则力求呈现出一种系统的汉代敦煌历史。诚如郑炳林教授所言,本书“远远称不上是两汉敦煌历史研究的终结,而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在之后的持续研究中,书中的部分观点还在不断的得到修正、补充和完善,但这并不影响本书成为两汉敦煌历史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从空泛转向具体的一次积极尝试。
目 录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敦煌的早期历史
第一节 敦煌名称的起源与丝绸之路的开启
第二节 秦至西汉前期的敦煌及河西
第三节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与对河西的占领
第二章 西汉敦煌郡、两关的设置与移民实边
第一节 西汉敦煌郡的设置与敦煌城的修筑
第二节 西汉敦煌郡玉门关与阳关的设置
第三节 西汉对敦煌郡的移民
第三章 西汉经敦煌对匈奴、南羌的经营
第一节 西汉经敦煌及河西对匈奴经营
第二节 西汉经敦煌对南羌的经营
第四章 西汉经敦煌对西域的经营
第一节 西汉经敦煌开通南道及经营鄯善
第二节 西汉经敦煌开通北道及经营车师
第三节 天马传说、骏马贸易与李广利征大宛
第四节 西汉敦煌居卢訾仓城修筑与归属
第五章 新莽至东汉初年的敦煌郡
第一节 汉新之际敦煌及河西周边局势的恶化
第二节 新莽经敦煌对西域的治理
第三节 新末至东汉初敦煌及河西地区的归属变迁
第六章 东汉河西战略定位变迁(上)
第一节 光武帝对河西的接管及对凉州的战略定位
第二节 明帝进击北匈奴、西域与河西定位的调整
第三节 章帝时河西地区经济与外交功能的凸显
第四节 和帝至安帝初年凉州边塞形势的转变
第七章 东汉河西战略定位变迁(下)
第一节 “弃凉州”之议始末与牵制叛羌的新定位
第二节 安帝至灵帝时期河西军事价值的提升
第三节 凉州人控制下的东汉政府与凉州之间的关系
第四节 曹操控制下的东汉政府对河西的经略
第八章 东汉敦煌郡的职官考察
第一节 东汉敦煌太守及其相关事迹梳理
第二节 敦煌设置的西域官员——以中郎将与西域副校尉为中心
第九章 东汉经敦煌对西域的经营
第一节 东汉经敦煌与北匈奴争夺伊吾、车师
第二节 东汉经敦煌对鄯善、于阗、莎车等南道诸国的经营
第三节 东汉经敦煌对焉耆、龟兹、疏勒等北道诸国的经营
第四节 东汉与北匈奴残部在西域的对抗——以永元八年(96)系囚减死“诣敦煌戍”为线索
结语
参考文献
前 言
《敦煌通史》是我完成《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及《敦煌写本碑铭赞研究》之后最为想完成的一项研究工作。我从事敦煌通史的研究工作实际上也正是从完成《敦煌碑铭赞辑释》的三万字序言“敦煌碑铭赞及其有关问题”开始,当时我仅仅是想完成一部关于敦煌归义军史的专著,然而在完成归义军史研究的过程中,开始将敦煌历史研究的时间往前追溯到西汉时期,从而将敦煌归义军史的研究变成了敦煌通史研究。因为我主要从事的是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敦煌史的研究,对敦煌早期的历史了解不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所以我们此前进行的研究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很难将整个敦煌历史连贯起来。就研究的上限来说,最多也就到十六国时期,至于两汉时期的敦煌历史可说是一片模糊,特别是西汉时期的敦煌历史更是模糊中的空白。直到真正开始展开敦煌通史的研究工作后,我最初设想的仍是敦煌通史中的两汉部分仅仅占一章,撰写内容方面也是偏重自己比较熟悉的部分,但是设想的大纲总是被研究的冲动打破,先是在研究过程中将西汉单独变成一章,而后扩展成两章乃至三章、四章,最后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两汉时期敦煌历史的内容达到了九章、三十余万字的体量。当然今天呈现到大家面前的这部研究成果——《敦煌通史•两汉卷》,远远称不上是两汉敦煌历史研究的终结,而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甚至这个头是否开得好,也还很难说。因为研究两汉敦煌史对我们而言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从研究的地理范畴来看,两汉时期的敦煌郡大致包括今敦煌市、瓜州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等地区。《汉书·地理志下》记载西汉敦煌郡下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县,到《续汉书·郡国志五》记载东汉时期敦煌郡的基本行政区划并未改变。
汉、唐是敦煌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两个时期,也是研究内容最为丰富的两个时期,前者有简牍资料,后者有敦煌文献。敦煌出土汉简数量众多,主要包括斯坦因等在敦煌地区搜集的汉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马圈湾汉简和悬泉置汉简等。其中尤其以悬泉汉简数量最为庞大、内容最为丰富,牵涉到西汉敦煌历史的方方面面,它不仅记载着敦煌的历史,而且也涉及很多关于敦煌周边的历史,特别是敦煌及河西的历史、敦煌与西域关系史,有着非常丰富的记载,这就为我们研究敦煌与河西诸郡、敦煌与西域的关系提供了方便。
《汉书·西域传》记载了西汉与西域诸国交往的主要内容,但还有很多交往都没有记载,或者记载非常少,敦煌汉简可以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帮助我们了解西汉敦煌郡在东西交流中的繁荣景象。如敦煌悬泉汉简记载了很多关于敦煌悬泉置迎送西域诸国使节的信息,包括这些来客所属的国家、接待他们的经过和接待标准及负责护送人员情况等等,这些内容在正史中或者没有记载,或者记载很少。另外,通过丰富的汉简记载,我们还可以得知敦煌市场上很多物品都来自于长安,敦煌居民主要是从中原各个地方迁徙而来,他们中有士兵,有罪犯,还有很多无法在中原生存的贫穷百姓。士兵们轮番戍守敦煌,分别戍守着沿边要塞或者前往西域的交通路线上的亭燧,经过一段时间就要轮换,而接送他们的任务就落在这些属于交通接待机构的各个置上。还有不同类型的罪犯,通过邮驿系统来到敦煌服刑,一旦刑满或者因减刑到期,再由这些邮驿系统将他们送回原籍。贫民、士兵、罪犯及其家属汇集在敦煌的同时也将中原各个地方的文化都带到敦煌地区,因此西汉时期敦煌地区的文化并不因为地处边地而落后,反而因为中原各色人等特别是官员犯罪徙边敦煌,使敦煌地区的汉文化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一样且更具有特色。东来西往的形形色色的人汇聚于敦煌,特别是外来的诸国国王、贵人以及他们派遣的客使会集在敦煌,使汉朝西陲边郡——敦煌郡逐步成为一个极具“国际性”的都会城市,屹立在中西交通的道路之上。这些珍贵而丰富的资料在悬泉汉简、马圈湾汉简等敦煌出土汉简中都有所保存,通过对敦煌汉简的梳理和研究,一个面貌全新的西汉敦煌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正史中关于新莽时期的敦煌郡记载也非常少,除简略记载车师后部和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等叛逃匈奴及王莽出兵征伐焉耆外,再无更多信息。敦煌汉简同样留下这个时期的很多记载,有些记载可以同正史相印证,有些可以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比如敦煌马圈湾出土的大量木简涉及新莽时期出使、征伐西域之事,这对研究新莽时期中原与西域的关系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另外,敦煌悬泉汉简记载有新莽始建国、始建国天凤、始建国地皇等年号的内容,表明敦煌郡的行政机构并未因为中原地区大乱而停止运转,而是仍然按部就班地处理其行政事务。因此敦煌汉简是研究新莽时期敦煌历史的珍贵资料,没有这些资料,很多历史的真相将会被埋没。
敦煌出土简牍属于东汉时期的较少,且有限的有明确纪年的汉简集中在东汉前期尤其是光武帝时期。因此在研究东汉敦煌历史时,所能利用的资料远不及西汉中后期及王莽时期丰富,我们只能尽可能充分地挖掘正史中的相关记载,当然在有些地方还是会结合汉简与敦煌文献的相关记载进行研究,以体现汉简与敦煌文献在敦煌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和作用。
总体而言,两汉敦煌历史的研究不仅要依靠正史,还应当关注敦煌出土的简牍资料,这些资料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全新世界。我们在对两汉敦煌郡研究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有意摒弃过去单一而简略的研究状态,从而转向更系统、多方面的具体探讨。因此,这些研究不管有哪些成绩或者不足,都可以对两汉敦煌历史从宏观转向微观、从空泛转向具体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这一研究过程能够为敦煌学界发展带来推动作用,哪怕这些研究得到的赞许远少于批评,还是企盼学术界能够更多地关注两汉时期敦煌历史的研究,这无论从哪些方面看,都是非常值得的。当然,因为两汉敦煌历史的研究是我们初涉的研究领域,所以研究中难免存在很多问题和错误,我们诚恳地希望学术界以各种方式给我们提出来,如果将来有可能,我们将在这部书的修订版中加以纠正。或许这个过程会长一些,但是一定会完成。
郑炳林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2022年3月11日


